上海常提“海派”,然而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1999年版的《辞海》都没有专门解释。
“海派这个概念的出现,要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2018年10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子善做客“行知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心中的海派与海派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子善做客“行知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心中的海派与海派文学
鲁迅对“海派”有过什么评价?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曾发表两篇标题几乎相同的文章,其一为1934年发表的《“京派”与“海派”》。
鲁迅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 ‘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当时鲁迅给“海派”下的定义为“海派是商的帮忙”,略带调侃意味。
一年后,鲁迅继又发表《“京派”和“海派”》一文,进一步分析说一年后京海开始合流,主要论据在于周作人为施蛰存所编《晚明二十家小品》题签。周作人被鲁迅冠之以“真正老京派”,施蛰存被鲁迅称之为“真正小海派”,而周施的合作即“京海合流”的体现。
“这两篇文章说明什么?说明鲁迅对‘海派’这个概念是不认同的,有批评的,与我们今天对海派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陈子善说,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海派,他必须把这个背景讲清楚。
“当年鲁迅对海派及海派部分作家有批评。现在看鲁迅的批评也值得被大家讨论。这个事实必须提出来,我们不能回避。当年鲁迅对海派的理解就是海派是近商的,实际上就跟金钱走得很近,这是鲁迅的看法。”
哪些作品与作家可以归入“海派”范畴?
在陈子善看来,今人既没有必要完全拘泥于鲁迅的论述,亦不能将鲁迅批评过的“海派”丢入历史故纸堆。如何重新定义“海派”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以文学为例,到底哪些作品可以归入“海派”的范畴呢?
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海派小说”专辑,收入十个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包括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李同愈《忘情草》、崔万秋《新路》、林微因《花厅夫人》、苏青《结婚十年正续》、施济美《凤仪园》、丁谛《前程》、予且《两间房》、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东方蝃蝀《绅士淑女图》。丛书主编魏绍昌先生认为上述作家是海派小说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属于海派小说的一部分。
在这十本小说集的影印说明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话:“所谓海派,是指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畸形的都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而言……他们都以上海人的眼光和心态写上海滩上的形形色色,作品语言渗透着洋场气息和浓郁的上海风味,以故事生动、内容通俗,适合多层次读者口味为特色。”
“就这么一段简明扼要的话,就有对海派文学的界定或者评价,当然这里面也有批评,譬如说‘畸形的都市环境’。”陈子善猜测这段话就是魏绍昌先生写的,“我基本上认同魏先生对海派文学的评价。”
到了1999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者许道明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海派文学论》。这是一本专门讨论海派文学的学术专著,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地讨论海派文学。
“许先生对海派文学有很系统的研究,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另一套书,是他编的,叫做《海派小品集丛》,小品就是散文,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分了好几辑。”陈子善说。
也就是在《海派小品集丛》中,海派文学家的名单更长了:施蛰存、徐訏、叶灵凤、章衣萍、张爱玲、丰子恺、钱歌川、章克标、无名氏等。

海派文学何以起步?
陈子善认为,晚清、清末或民国初年是海派文学的起步期。
“实际上海派文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上海文学当中重要的一支,主因是清末上海开阜以后,印刷资本主义兴起后,上海市民阶层不仅有在上海赚钱的需要,也有文化消费的需要。他们需要阅读。除了古典名著之外,除了地方戏剧之外,除了已经开始引进的电影之外,他们需要更多的阅读。这时候文学创作欣欣向荣,诞生一大批作家、作品。”
其中有一部作品非常重要。陈子善说,那就是清末韩邦庆用苏白写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当时在上海做生意的很多是苏州人。这部长篇写的是乡下人进城。对上海的海派文学来讲,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写‘乡下人进城’,一直写到今天农民工、乡下人进城。当时都市文明、都市文化正在兴起,上海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新兴移民城市。”
”这部小说写得很生动,从当时社会的某种程度来讲,可以说是上海社会的百科全书。”陈子善还认为,海派文学的开山祖师就是《海上花列传》。
在韩邦庆之后,还有很多写上海的作家,陈子善认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为海派文学,比如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新上海》等。“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有很多分类,有的是黑幕小说,有的是情爱小说,但是我也可以把它们归入海派文学。我认为海派文学最初是这样起步的,写上海滩的形形色色。”
陈子善说,到了三十年代,新文学起来了,成为上海文学的主流,但是写上海的文学家仍然在写作,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有一些新文学作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文学一方面要向外国学习,一方面要向古代文学学习,向《红楼梦》、古典四大名著学习。那有没有可能也向近代以来写上海的作家学习,即向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家学习呢?”
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叶灵凤,他写了长篇小说《时代的姑娘》《未完成的忏悔录》,结果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连载,一举成功。
“这是海派文学在三十年代的收获。叶灵凤是新感觉派的一个作家,所以他把先锋现代小说的技法运用到通俗的大众的连载小说上面,符合当时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后来他又在小报上连载《永久的女性》,写一个模特的爱情生活,这故事都发生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陈子善认为,这些三十年代中期的长篇连载小说是海派文学的收获,同时也是新文学向通俗文学学习借鉴的收获。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对海派文学原先的界定,我也可以说新感觉派其他的作家,譬如说穆时英写的一系列上海都市题材的作品,我也视之为海派文学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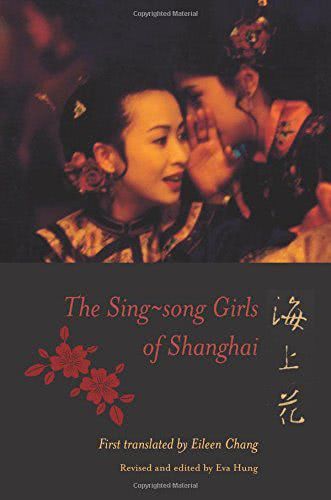
在宝山“行知读书会”,陈子善还特别提及学美术出身的宝山人滕固。“他前期作品有唯美派的倾向。小说创作出过好几本,比如《迷宫》、《外遇》等。他的作品流露出当时在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的颓废生活,他们的苦闷,他们的追求,这是滕固。
“我们宝山现在好像很少提到滕固这样的作家,但他在上海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低的。而且他的这些作品,如果我们把尺度放宽的话,也应该是海派文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我特别要提出滕固,是因为上海是移民城市,在文学上成就特别大的上海人不是很多。浦东有傅雷、松江有施蛰存,宝山有滕固、嘉定有秦瘦欧和唐大郎,他们都值得我们自豪的。”
海派文学贴近上海百姓,今后何去何从?
到了四十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大批海派作家。陈子善举例,作家周天籁写了一个长篇《亭子间嫂嫂》,那是典型的海派小说,写上海底层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了一个文人跟一个在亭子间里面的女子,这个女子为生活所迫接客,“是很感人的作品。”
而海派文学在海外产生影响,陈子善认为要以刘以鬯为代表。
“刘以鬯是上海出去的,他的文学道路在上海开始的。他的特点第一继承了上海、海派的文化传统;第二,他擅于向西方学习,他后来在香港出版了一个长篇小说《酒徒》就是意识流手法写的,他是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有多种写作手法的作家。他还写通俗小说,一般纯文学看不起通俗的,认为纯文学才是文学的正宗,通俗的也不大愿意跟纯文学的来往。但刘以鬯先生不一样,他后来的长篇《对倒》被王家卫改编成电影《花样年华》。”
在陈子善看来,海派文学有一个特点——贴近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我刚才讲的那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贴近生活,不居高临下,这是海派文学很大的特点。”
“我们今天讲的海派文学,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几部作品绕不过去。比如《海上花列传》《亭子间嫂嫂》《传奇》《结婚十年》都可以视为1949年以前海派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可能还有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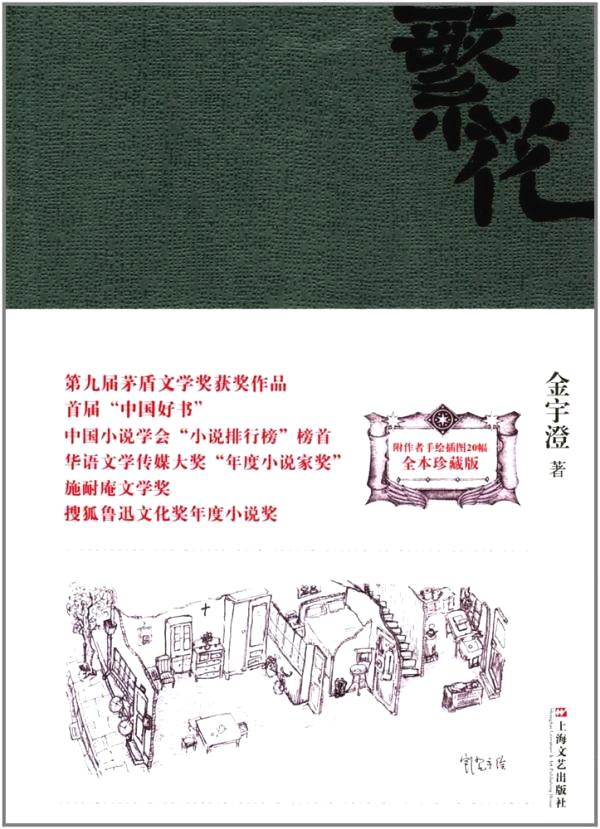
金宇澄的《繁花》在陈子善看来是当下海派小说非常成功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还可以提到哪些海派文学作品呢?陈子善说,我们可以提到《长恨歌》,虽然王安忆一定不会说自己是海派作家,但是我们可以把她这部作品归入海派文学之列。而金宇澄的《繁花》在陈子善看来也是当下海派小说非常成功的作品。
“海派文学有几个基本的特点。一个它的开放性、多样性。因为是写上海,上海本身是开放多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在海派小说中体现得很充分。二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带有探索性,为什么呢?原来两条路,新旧文学互相敌对,海派文学却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探索。”
“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海派文学往何处去,今后怎样进一步发展?这是要大家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陈子善说,上海是个丰富的城市,写弄堂的好作品不少,但如果只写弄堂,就显得单一了。
“上海的郊区如何写?城郊结合部如何写?工厂如何写?打工者、外来者如何写?海派文学的特点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在回顾海派文学时,对于海派文学产生的新的期待。”( 摘自澎湃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