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先生的这句话是理解文学书写的总钥匙。2019于上海作家而言,是小说创作版图中较为丰硕多样的一年。孙顒、唐颖、朱大可等五零后作家持续推出中篇佳作,小白、姚鄂梅、禹风、薛舒等六零和七零后作家展现出“喷涌”强劲的创作势头,周嘉宁、王占黑、王苏辛、王侃瑜等一批八零和九零后作家显出日益成熟和锐不可当的创作态势。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作家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钟山》《芙蓉》《长江文艺》等五十余家国家级、省市级主流文学期刊上共计发表较有影响力的中短篇小说七十余篇,其中中篇小说二十余篇,短篇小说五十余篇,多篇作品被《思南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

纵观这些作品,既有对这个光焰四射时代日常生活、精神现场的不同凝视,也有对个体生存苦难、人性善恶的深度拷问。上海作家怀揣以小说抵达现实和心灵的梦想,展示了他们的创作活力,以及对中短篇小说新的可能性的挖掘。
直击现代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现场
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绕不开当下,它有可能不把读者带往喧闹的中心,而是可能带到偏僻的区域,因为那里可能会发现某些被遮蔽的、细小的事物,这些细微与被忽视很有可能才是生存的真相。对当下日常生活和精神现场的关注依然是本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
孙颙中篇《蚂蚁与人》是女知青的成长史,关乎女性的城市生存、精神成长和时代处境。小说中的女主上山下乡、从下到上的突围过程是当代青年奋斗打拼的成功典范,带有时代印记和励志作用。但小说的叙事重心在于女性内心情感的自我追溯与审视,在于对女性处境的深切体察。经历了物质和婚姻的双重锤炼,女主角才滋生出真正的女性意识。“蚂蚁镇”正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背井离乡奋斗拼搏者的起点,作者把人物置于变幻莫测的时代浪潮和诚信缺失的婚姻博弈中进行刻画,有沉重的历史感。
唐颖短篇新作《隔离带》讲述的是她再熟稔不过的上海中年女性的婚后生活,讨论的是现代都市的人际关系。小说中的“我”和丈夫物理上是“零距离”在共同生活,但“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患过肝炎的丈夫对病痛、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听任闺蜜礼平的建议草草换房,从此二人渐行渐远,最终婚姻走向了终结。小说呈现了现代人貌似最亲近稳定的闺蜜、夫妻关系之间,也存在看不见且无法跨越的“隔离带”,或隐形或有形,它如沉默的暗礁,影响着命运的暗流走向,又似移动的镜子,能够照见人物的内心裂痕,作品是对现代人外在表现与内心真实两者间距的揭示。她的另一短篇《烈饮》中,女主人公哲子不停寻找有趣的灵魂以及高度的精神默契带来的激情,写出了孤独都市女性的某种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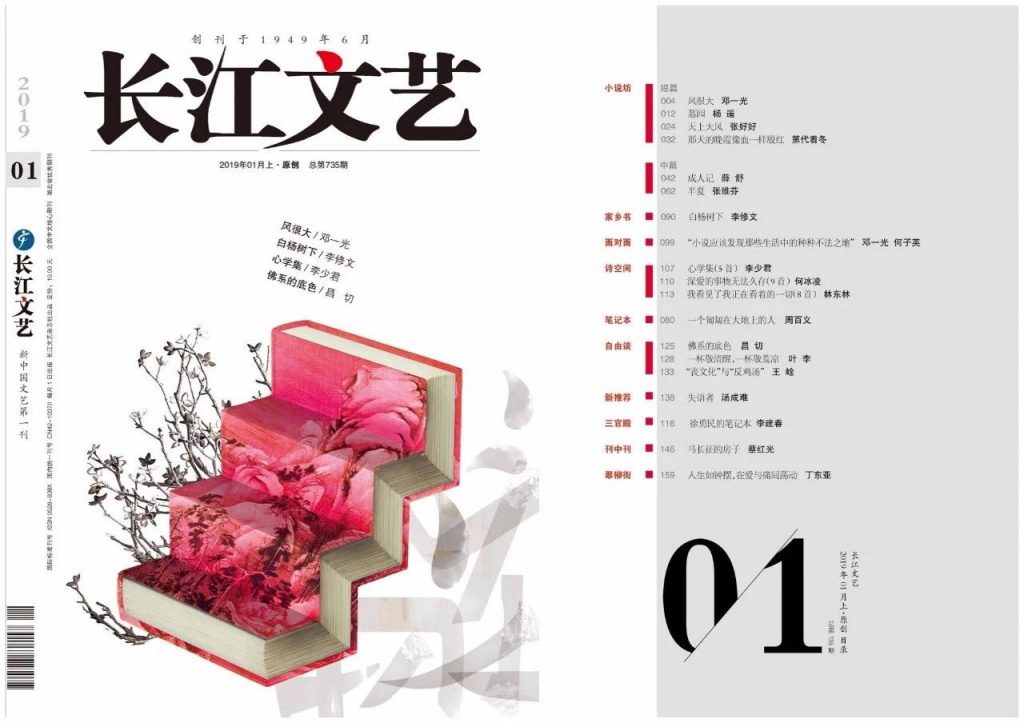
薛舒近几年中短篇小说数量惊人,从《隐声街》里的智障者大毛毛到中篇新作《成人记》里的智障者郑舟,目光所及都是特殊人的日常与处境,她有意无意间试图带领我们走进这片隐秘的世界。《成人记》讲述了单身母亲严月独自拉扯智障儿子郑舟长大的故事,笔墨虽集中在母亲和儿子的生存困境,但作者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在家庭层面上叙说母性力量,她还有更深的寓意——这也是男孩性觉醒的见证报告。借助母亲严月的内心慌乱与挣扎,薛舒说服并教会了我们,如何做才能不把他们当“病人”。
她的另一中篇《此处可以无声》则透露出她对少女的成长有着很深的体察,她了解女性,进而通过作品来呈现她的人生经验。作者把女孩周晓闵的早恋问题与二十年前 “我”与政治老师赵天骥的往事并置在一起,营造出多层次叙述结构,当画面转回到现实场景的同学会,跳脱出的是清晰地理性,达到了理解过往和构建自我身份的写作目的。“我”与女孩周晓闵的交往又构成了一场生命的相互映照,小说对青年的成长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同样是对“病人”个体的观察与剖析,三三在短篇小说《唯余荒野》中采取地是隐晦的提及。小说中暮年的“我”与前夫邵老师久别重逢再续婚缘,而他的弱智妹妹早娘却用近乎变态的恨意报复自己。在一次次地亲情与爱情的较量后,留下的是虚无与灰烬,女主也从命运之门中终于觉醒,感同身受到了早娘变态恨意背后的无奈和痛苦。三三很轻易就把我们带入了女性挣扎的困境中,藉由人物曲折的情绪流动,三三勘测出了人心深处那些偏执与包容、敌视与宽恕、患难与共和同床异梦的隐秘地貌。

当身体陷入巨大困境逃无可逃时,现实的利益都可以当做条件拿来与身体形成交换,而当生命被置放于任人摆布的天平上去衡量时,生活带来的伤痕也很可能随之而来。禹风中篇小说《下降流》讲述了男主角莫滔在阿罗娜海滩潜水的故事。通过两组人物在潜海过程中的不同表现,禹风巧妙地诠释了爱与占有、嫉妒、牺牲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暗示人生就是要背靠永恒之困境向死而生勉力前行,坦然接受生活和命运的各种意外。小说入选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榜。
写小人物几乎是王占黑创作的一个法则。中篇小说《痴子》我读到了三位身体各有缺陷的中年男人的窘迫与狼狈。作品也是王占黑游走于城市街头的一篇纪实,街角的报亭、楼顶违章建筑鸽笼、网红小餐店甚至流浪汉聚集地的桥洞都是她追赶与关注的对象,这些地点已不仅仅是小说人物嗡鼻头赵益民、瘸腿阿兴及傻瓜秦美中的生活背景因素,它们其实被作者推到人物命运的前台,成为当下真实生活的对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王占黑还给予了宽恕新的定义——嗡鼻头跨越时间的河流重新面对曾经施予他伤害的粟凤来,给出的是爱的应答,选择了赦免与挽救,这是作者对人生苍凉的抚摸。
鲜明的语言特质,文本内外的探索
米兰·昆德拉说过:追求的终极永远是朦胧。这种朦胧感体现在小说文本中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语言风格,而风格在几位上海作家笔下都有鲜明的特质,他们让日常阅读产生了不一样的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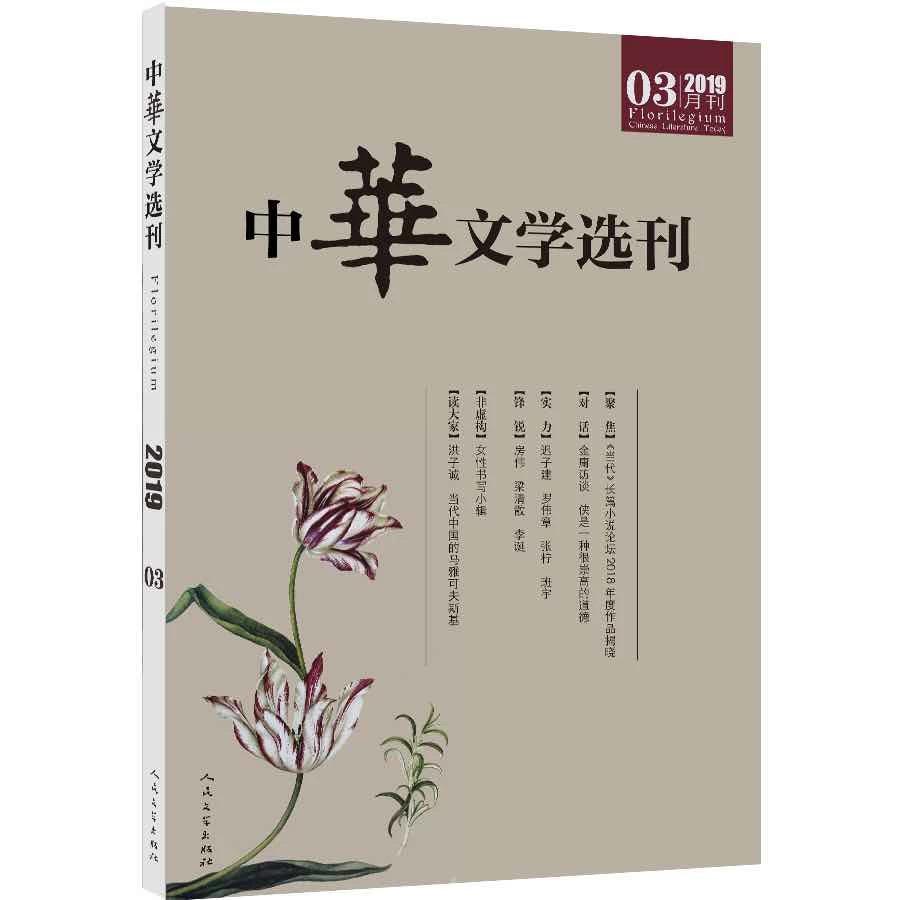
阅读朱大可《香道师》和哥舒意《祁雨娘》除了语言上的愉悦感之外,还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叙事气质:典雅,优美而沉郁,充满古董似的气味,又富有想象力和传奇性趣味。短篇小说《香道师》讲述了阴阳同体“太极人”白萱的故事。香道师白萱的女性躯体内共存着她的“恋人”弟弟白朗,雌雄同体的二人是循环的连续体,相见就是死亡,开始也就意味着终结,潜心研制男性迷情香的她最终倒在了与弟弟首次相见的夜晚。作品融合了中国古代香道文化、阴阳人等江湖传说,可谓志怪之集中呈现,打造了奇特的嗅觉体验。同样是对东方古老传说的书写,短篇小说《祈雨娘》讲述了我和女孩雨城的故事,哥舒意塑造了以舞来祈雨的雨城娘形象,故事之下实则是他对人与乡村、人与空间的思考,他对城市进程及生活变迁的理解超越了表面华丽的符号。

小白也是很有耐心的作家,叙事冷静、简约,专致于在极简的文字中不断深潜,将本质或内核从故事表相的包覆中揭出。无论是《透明》中的私人侦探“我”,还是《婚姻风险》里人工智能系统“我”,小白都设置了多层有意味的对话,交叉存在着几种声音。通过“我”地独白,分别呈现出马琳和秦晓东两对夫妇间的矛盾和裂痕,两部小说都是对当下都市婚姻生活的探讨,作者对夫妻关系中“距离”的发现与捕捉,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伦理秩序和婚姻问题提供了多样化参考。小说中的对话和独白使得文本具有多重解读的意蕴,“我”独白是外指的,指向现实和生活,是小说意蕴生成的背景;而“我”与两对夫妇的对话是内指的,是小说深入展开的科幻主体,作者为科幻想象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折叠”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王侃瑜也是近年活跃的科幻作家,《语膜》讲述柯莫语语言老师伊莎与儿子雅克之间的故事,伊莎加入跨国翻译服务公司巴别的柯莫语翻译项目,试图用自己的语言习惯帮助巴别建构柯莫语语膜。文本表象是探讨语言的科幻小说,但核心是写人物的内心挣扎以及亲子关系的讨论。她的另一短篇《链幕》同样延续了这一风格,小说中弟弟陈淮是患有自闭症的青年,他长期自我隐藏在能够储存语言的智能链幕背后,直到他意外去世后,通过警方的调查姐姐陈渊才真正了解了弟弟的生存状况。小说中科幻只是点染,母题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理解,或永远无法互相理解,以及隔阂如何产生,又是否有可能真正消除隔阂。同样是科幻作品,负二的《身躯》带来了另一个AI模型,小说讲述了一个智能躯体的故事。
王苏辛同样有着强烈的个人写作风格,她的小说虽然会涉及到乡村与城市,但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城市经验与乡村题材,她有有与众不同的故事讲法和节奏。中篇小说《东国境线》中的男主高中老师郑东阳不再与人交流,喜欢独自画画并制作Excel表格收集老建筑图片和坐标,不仅妻子徐虹对他这种令人陌生的变化感到愤怒,同事柳方蒙对他的异常也很疑惑。通过对郑东阳妹妹郑东兰、前妻宋博以及曾经使用过的博客进行追踪,柳方蒙逐渐拼凑还原出那个真实的郑东阳。作者把主人公置于父母离异、丧子又再婚这种极致化的生活处境中,通过独特的视角将人物精神困境一步步揭示出来,既有情感上的跌宕起伏,也有近乎悬疑的故事线索,让作品充满了探索精神。

王若虚《封腰无用》与王莫之《老父还乡》则是对当下“写作者”群体的观照。两篇作品中,文学青年秦玉玺、编辑小李都过着卑微且琐碎的生活,出书、版权纠纷等都是当下文学界的现实疑难,但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指明出路。在两位作家细腻朴实的文笔和熨帖的上海方言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都市 “写作者”的真实生存境况。
作家的自我打开和突围
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拥有个人风格,风格相当于节肢动物的甲壳,在很长时间里能够提供保护。然而,要持续成长,铠甲终有一天会成为束缚,成为皮肤上如影随形的桎梏。突围和挣脱它是痛苦的、艰难的,但这又是非常必要的,作家如何在小说中打开自己并进行突围,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高产的姚鄂梅,不是一个追赶热点的作家,有她的独特坚守。比起追踪时代的风象,姚鄂梅更经常写的是成年女性的隐秘或家庭里那些不能释怀的。《外婆要来了》讲述了医院保洁女工李南和花房男花工老鲍之间的故事,李南为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潜伏在医院只为找到那个曾经“接”走她孩子的“外婆”,产科“弃婴”处理的真相逐渐被揭穿。《基因的秘密》写家族里的男性逐个遭遇不幸的故事。两部作品我们不仅能看到姚鄂梅以文学来确证生活的意义,还有她主动将使命感灌注在写作之中——“把我归为生活和作品的一部分”,试图从道德轮回的角度去寻找复杂多变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她对人生的反思和对痛苦的体认。

李西闽的中篇小说《无处告别》是一个人的自我打开,是写男性的城市生存、婚姻成长和时代处境。作品讲述了因婚失意并患有绝症的男子宋杨,从上海来到西部小镇榆树镇“寻死”的故事。在小说人物结构和语言上,作者采取了写宋杨的婚姻故事和他在小镇所见所闻双重叙事结构。作者写出了当代中国式婚姻关系的复杂,也有对男女不同表现的反省和表彰。
张怡微的小说里同样没有反讽、没有魔幻、没有荒诞,她选择以温情的、慈悲的语言谈论生活、谈论家庭。《缕缕金》里的女孩邱言和《醉太平》里的男孩林太吉都是失落的人,两位青年都深深陷入家庭的泥淖,他们是在人群里安静无声的人,只能躲在长着青苔的拐角处,目送母亲或父亲逐渐远去的背影。在表达“无根”“漂泊”“代沟”这种富有时代性、人类性的题旨时,张怡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父辈往事与爱情絮语,而是以人物意识的镜像来确认小说中自我的突围。
周嘉宁的中篇小说《再见日食》讲述了日本小说家拓重回美国佩奥尼亚小镇参加葬礼的故事。通过追忆男主二十年前在此参加艺术家培养项目时期的青春成长、感情遭遇和心理体验,也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对爱情的叹息。虽然组织者乌卡的逝世、泉的杳无音信等都是沉重而残酷的细节,但阅读完之后却并不黑暗,因为小说内核指向的是成长轮回与和自我超越。因为青春从来不是真空无菌的文体,恰恰当拓从少年向成人转变的这个过程中,他懂得了如何去平衡遇到的温情或残酷。

谈到作家个人突围,近几年上海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跨界”现象也愈发普遍。前有于是、黄昱宁、项静等翻译家、评论家加入小说创作队伍,今年评论家李伟长也带来“反向实验”短篇小说《祥少爷》,这种“跨界”创作能够反哺文学批评,促使评论家们开展文学评论时更富于感性认知。
诚然,本篇盘点无法尽数解读一年来的作品及上海作家的创作密码,只能呈现一些文字镜像的碎片。从中也可看到小说创作艺术的复杂性,有些作品依然拘泥于狭窄局促的现实无法走出,也暴露出当下同质化写作的困境。虽无法穷尽,但不少上海写作者的那些真诚和纯粹:直击困境,用故事追踪,并发出对于他者和广大世界的体恤,值得我们为之驻足。
作者:李鹏(上海市作家协会创联室)


发表您的见解